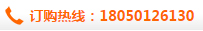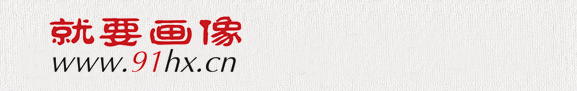肖像畫被中國(guó)古人稱為“傳神寫照”、“寫真”。畫絕、才絕、癡絕的大畫家顧愷之畫人,數(shù)年不畫眼睛,別人問他為什么,他說:“四體妍蚩本無關(guān)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他畫“俊朗有識(shí)具”的名士裴楷在其臉上加三根毛,他畫“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的名士謝鯤將其放在巖石中,目的只有一個(gè),就是表現(xiàn)對(duì)象的風(fēng)姿和神態(tài)。從自顧愷之至任伯年的肖像畫來看,或者從王繹的《寫像秘訣》、蔣驥的《傳神秘要》、沈宗騫的《介舟學(xué)畫編卷三·傳神》、丁皋的《寫真秘訣》等肖像畫論著來看,記錄與再現(xiàn)從來不是中國(guó)傳統(tǒng)肖像畫的主要目的。而且元代文人畫的興起之后,肖像漸漸成為中國(guó)傳統(tǒng)繪畫之末流,不但排在山水和花鳥之后,而且排在故事、風(fēng)俗、道釋、仕女之后,與達(dá)·芬奇(Leonardo Da Vinci)《蒙娜麗莎》在文藝復(fù)興繪畫中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
15世紀(jì)30年代尼德蘭畫家楊·凡·艾克(Jan van Eyck)和胡伯特·凡·艾克(Hubert van Eyck)兄弟在坦培拉技法和混合技法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比較完善的油畫技法并畫出了著名的宗教畫《根特祭壇畫》和肖像畫《阿爾諾芬尼的婚禮》。油畫傳入中國(guó)見諸史料的記載是,1582年萬歷十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guó)并將天主像和圣母像呈獻(xiàn)給皇帝,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另一位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再次來到中國(guó)成為宮廷畫師,經(jīng)歷康、雍、乾三朝發(fā)展出一種中西折衷的繪畫。事實(shí)上,早在利瑪竇來到中國(guó)之前一個(gè)世紀(jì),福建莆田縣的一對(duì)門板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用油彩繪制的身著漢裝的西洋美女肖像畫——“木美人”,可見油畫出現(xiàn)之后不久就已經(jīng)傳入中國(guó),迄今已有五百余年的歷史。然而油畫在傳入中國(guó)之后的四百年間僅僅承擔(dān)著宗教宣傳的任務(wù)并被視為攝影術(shù)產(chǎn)生之前記錄和再現(xiàn)的一種“奇技淫巧”,因此一直沒有被知識(shí)階層接納。油畫在中國(guó)真正成為“藝術(shù)”始于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的西學(xué)東漸之際。受到“五四”前后“全盤西化”的影響和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的感召,中國(guó)畫家紛紛留學(xué)日本和歐美學(xué)習(xí)油畫,1919年之前有李叔同、李鐵夫等人,之后有徐悲鴻、林風(fēng)眠、龐薰琹、劉海粟等人,他們回國(guó)后或興辦學(xué)校或參與教育,油畫作為一種藝術(shù)類別在中國(guó)落地生根。
從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中,“毛澤東”、“三突出”和“高大全紅光亮”一直是中國(guó)肖像油畫的主流。它們與20世紀(jì)80年代初的“傷痕美術(shù)”、“鄉(xiāng)土寫實(shí)”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羅中立的《父親》、陳丹青的《西藏組畫》、何多苓的《春風(fēng)已經(jīng)蘇醒》等等以“人”和“人性”為主題的作品拉開了中國(guó)油畫“百家爭(zhēng)鳴、百花齊放”的序幕。尤其是羅中立的《父親》,中國(guó)農(nóng)民苦難、滄桑、悲壯的頭像出現(xiàn)在“領(lǐng)袖像”一般尺幅巨大的畫布中,而且畫家運(yùn)用了絲絲入扣的照相寫實(shí)技術(shù),營(yíng)造出動(dòng)人心魄的視覺沖擊力,因此極具象征意義。20世紀(jì)80年代最后五年(1985年-1989年)的“新潮美術(shù)”貌似繁榮,實(shí)則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各個(gè)流派的中國(guó)“山寨”版,喧囂之后并沒有留下什么有價(jià)值的作品。盡管如此,這一運(yùn)動(dòng)猶如大戲開場(chǎng)前的鑼鼓,把人們的目光引向世紀(jì)之交。
“新古典風(fēng)”畫家多數(shù)是學(xué)院派肖像畫家,其中朝戈是最獨(dú)特的一位,他在油畫《敏感者》中塑造的表情焦慮、頭發(fā)胡須凌亂的男人已經(jīng)成為20世紀(jì)末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最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朝戈的肖像油畫著力表現(xiàn)“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的古典精神,這種古典精神通過“蒙古人”的肖像傳達(dá)而顯現(xiàn)出當(dāng)代性。“新生代”畫家中的杰出代表劉小東早年從研究盧西恩·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的直接寫生方法入手,從中發(fā)展出一種直抒胸臆、肆無忌憚的肖像油畫語言。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平淡、無聊、荒誕、幽默、殘酷、冷漠被藝術(shù)家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比如他的大型創(chuàng)作計(jì)劃兩組《溫床》和《十八羅漢》。石沖的肖像油畫實(shí)現(xiàn)方法非常復(fù)雜,“生命”的主題卻十分單純。他往往從觀念出發(fā),然后制作裝置、拍攝照片,最后再憑借高超的寫實(shí)技術(shù)呈現(xiàn)在畫布中。從《欣慰中的年輕人》、《今日景觀》到《外科大夫》、《某年某月某日的肖像》,石沖的肖像油畫其實(shí)就是“裝置藝術(shù)架上化”一個(gè)嘆為觀止的結(jié)果。忻東旺的肖像油畫大都從直接寫生中來,其寫生能力在圈中有口皆碑,全國(guó)美展金獎(jiǎng)的榮譽(yù)便是證明。從頭像《亞麻李》到全身像《保衛(wèi)》再到群像《早點(diǎn)》和《裝修》,忻東旺創(chuàng)造的鮮活生動(dòng)的“村民列傳”系列形象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代中國(guó)城市化進(jìn)程中一個(gè)獨(dú)特的文化景觀。毛焰的繪畫顯示出純粹個(gè)人化探索的驚人能量,他的油畫中肖像的主題一以貫之,甚至具體模特也一以貫之。如果說上個(gè)世紀(jì)90年代毛焰以朋友為主題的肖像畫還帶有明顯的“古典表現(xiàn)主義”特征的話,那么新世紀(jì)以來毛焰千變?nèi)f化的《托馬斯》系列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一種恍惚混沌筆墨氤氳的東方意境,你可以認(rèn)定那是人物,也可以認(rèn)定那是山水。
除此之外,在“政治波普”和“玩世現(xiàn)實(shí)主義”土壤中生長(zhǎng)出來的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F4(張曉剛、方力鈞、王廣義、岳敏君)也對(duì)“大肖像”情有獨(dú)鐘,無論黑白灰還是紅黃藍(lán),亦無論一本正經(jīng)還是嬉笑怒罵,他們的文化基可以追溯至羅中立的《父親》,乃至“文革美術(shù)”。
五百多年前,尼德蘭人發(fā)明了油畫,但油畫并不就是尼德蘭人的專利。油畫豐富的表現(xiàn)力令它傳遍西方、傳至中國(guó)。中國(guó)古往今來總是在固有文化的基礎(chǔ)上吸收外來文化進(jìn)而形成新的文化并且生生不息。正如佛教傳入中國(guó)而產(chǎn)生了禪宗一樣,油畫傳入中國(guó)也必將產(chǎn)生新的中國(guó)油畫。
笛卡爾(Rene Descartes)曾說:“人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則說:“藝術(shù)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來的形而上活動(dòng)。”從威倫道夫的維納斯(Venus of Willendorf)到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的《瑪麗蓮·夢(mèng)露》,一部藝術(shù)史就是一部關(guān)于“人”的視覺文化史,肖像藝術(shù)一超直入地再現(xiàn)“人”、表現(xiàn)“人”、結(jié)構(gòu)“人”、解構(gòu)“人”,其永恒的魅力穿越古今、跨越中西。
我想,肖像只是一類主題,油畫只是一種媒介,二者終將被超越,“國(guó)際化”與“中國(guó)化”都不重要,惟有個(gè)體生命精神的真實(shí)體驗(yàn)才是藝術(shù)永恒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