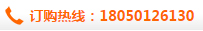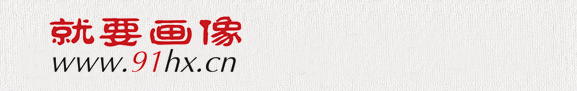徐里,1961年生于福建,1985年畢業于福建師范大學美術系油畫專業。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分黨組副書記、秘書長,中國文聯、財政部、文化部“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組委會辦公室兼創作指導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作品連續入選第七至十一屆全國美展。
徐里28歲以一幅油畫《天長地久》獲第七屆全國美展銅獎后,又連續五屆以完全不同的油畫面貌入選全國美展,在油畫與民族文化的融合上不停歇地探 索,被詹建俊先生稱贊為“這一課題自覺的實踐者”。近年來,他用油畫表現的“中國山水”系列,更是廣受贊譽。近日在京舉辦的“徐里水墨藝術展”,展現了其 在油畫創作之外的另一種藝術面貌。
剛剛上任中國美術家協會黨組副書記、秘書長的徐里接受了《美術文化周刊》的專訪。在短短一個小時里,他還收到近10個電話和短信,接待了三四批來訪者,處理了幾個亟待審核的工作文件。他抱歉地對記者說,別人可能無法理解美協工作這么繁忙,而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狀態。
徐里介紹,今年適逢第十二屆全國美展,有13個展區將會同步進行,這13個展區要籌備、初評、復評、開幕;還有幾十項全國性的學術展覽已經排上 日程,而美協23個藝術委員會的各種活動和展覽也需要協調,以及對外交流和國內的重大主題性美術活動、會員發展等等,“可以說忙不完,一上班,進了辦公室 就出不來了”。
在他的辦公室里,張貼著兩張畫滿標記的地圖,一張是世界地圖,一張是中國地圖。兩張地圖上,密密麻麻地畫滿了線條,每一根線條的背后,就是他的 一次行程,而每一次行程背后,又都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也要畫萬里畫。通過寫生,把自己的想法、觀念升華提高了。”對寫生充滿熱情的 徐里,就這樣聊起了他的藝術創作。
美術文化周刊:你的日常工作狀態需要的是嚴謹、條理,而回到創作時,又需要自由、放松的狀態,你如何安排時間和進行這兩種不同狀態的切換?
徐里:作為畫家,我只能把腦袋切換成兩個。首先行政工作不能受影響,工作時間就是工作,要把事情處理好,把本職工作做好,不然對不住全國美術家 的信任。工作之余,如果有一點時間對我來說就非常重要。我就像電閘的開關一樣,馬上要進入到創作的狀態中,對于一般的畫家,這可能很難想象。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風格的工作。一個是要非常嚴謹,按部就班地把每件事落實好,一個是非常放松、自由、富有想象力,還要有靈感的創作狀態。這兩種狀態有時是矛盾的,但可能是因為長時間習慣了用行政工作和藝術創作兩條腿走路,所以才能做到這種快速轉換。
另外,幸好我的工作與藝術創作也有一定的關聯。一個人創作水平的高低,除了技巧之外,同經歷、閱歷、視野等綜合要素也有關。我的工作,有很多是其他藝術家沒有經歷和感受到的,我平時看到的、思考的問題,在我的藝術創作中也是一種互補、充實。
還有對時間的把握。有些畫家時間很多,但一年畫不了幾張肖像油畫,因為時間太多了,就不一定珍惜時間。我的時間很少,就只能把有限的時間利用起來。在創作中比較有目的性,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哪些需要突破,所以效率相對更高。
美術文化周刊:你的創作,從早期西藏的“吉祥雪域”系列,到“永恒的輝煌”西域之旅系列,再到“藏密佛像”系列,一直到今天的“中國山水”油畫系列,從風格上總是每隔幾年就讓人眼前一亮。就你的創作而言,追求的是什么?
徐里:我近些年的創作,在嘗試不同的畫種、不同的形式風格,但所有的變化都圍繞著不變的主題,即我追求的中國精神、中國境界、東方神韻。
我原來學油畫,接受的是西方的培訓教育方式。而油畫在中國100多年的發展歷史中,提出一個問題,即中國的油畫家如果永遠做西方藝術的學生、模仿者,一直追隨在西方的各個藝術流派的陰影下,那中國的油畫定制是沒有前途的。
藝術是沒有國界的,但每個民族都有各自民族的文化背景和藝術特質。所以,如何借助西方的油畫,把中國的人文情懷,把中國人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通過油畫語言表達出來,尤其是把中國的審美價值、文化精髓表達出來,一直是我所思考的。
我從原來的“吉祥雪域”“永恒的輝煌”這些系列,到后來的“中國山水”系列,再到直接用中國畫來表現,基本上是沿著這條路在慢慢地走過來。只是大家看到的表現形式有些不一樣,但有些東西一路走來是沒有變的。
美術文化周刊:你一直提倡中國傳統文化,并在作品中努力傳達中國的審美價值,這些探索在創作里應該如何把握?
徐里: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有著自己獨特的思維和表達方式,有很多經典值得我們去學習、傳承和發展。藝術沒有新和舊,只有高和低。藝術的發展,就是不斷地學習、繼承和超越。
一件好的藝術作品,要有地域特色,也就是我們說的民族特色,還要有時代特色。我們現代人畫的東西不可能和古代人畫的一樣,我們這個時代有什么是 需要我們去表現的,這對于我們藝術家來講是很重要的。所以民族性、時代性,加上藝術家的個性以及對風格形式的追求,這三者如果能夠結合得比較好,就可能畫 出比較好的作品。
講很容易,但實踐起來非常難。因為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留下的好東西太多了,怎么在前人的基礎上向前發展,非常難。比如中國畫,要講究畫家的修為、 修養,境界,所以不僅要研習書法、文學、美學、哲學等相關知識,還要能作詩、作詞等。現在能達到這一標準和要求的,少之又少。每一個時代真正優秀的藝術 家,能夠稱得上大師的藝術家少之又少,這不是靠自封的,而是要讓歷史來檢驗,讓時間來證明的。是不是能夠傳承古人又能夠引領未來,每個時代都是在向前發 展,這種發展不是革命性的,也不是斷層性的。
美術文化周刊:你剛剛展出的水墨藝術,展現了你在油畫與漆畫之外的另一種藝術風貌。作為一名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油畫家,為什么又開始轉向了中國畫的創作?
徐里:作為中國的畫家,如果對自己的文化研究得少,顯然對發展我們自己的文化會有缺憾。我雖然受的是西式教育,學的是油畫,但我很想從我們自己的傳統文人畫中汲取營養,從中找到一點突破。
2004年我開始跟隨吳悅石老師學習國畫,他的國學修養、理論水平、繪畫表現力等方面,我認為是國內最好的之一。傳統的文人畫很難,說來簡單, 但很講究,比如書法的研習,對線條的認識和理解,對筆墨的把握,個人的修養、境界等。很多人感覺很簡單,其實真正看得懂就會發現很難。傳統中國畫的訓練, 與現在西式的美術學院教育模式差異很大。
比如我畫的中國畫人物,人物造型簡潔,用筆線條都很概括,通過簡潔的線條要能表現出人物的造型,以及用筆的變化、意趣,中國畫里包含的一些要 素,要通過這幾根線表現出來,難度是很大的。除了對線的認識,還有用墨、用水都需講究,不管畫再大的畫,畫完后筆洗里的水還是干干凈凈的。
無論是什么畫種、什么風格,對于藝術家而言都是一個可能的選項,這取決于自己的審美理想、藝術理念和具體需要。因此,對于我而言,更為重要和長期堅守的,是中華文化的立場,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以此為基礎,再在具體的課題下進行具體的構思和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