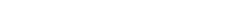繼美媒3月2日曝出克林頓肖像畫畫家故意在畫中留下一抹象征克林頓與萊溫斯基性丑聞的裙影后,美國記者馬克·哈德森(Mark Hudson)又羅列出了10幅暗藏玄機的油畫。
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阿卡迪亞的牧人》(巴黎盧浮宮)
著名畫家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 的杰作《阿卡迪亞的牧人》 (《Et In Arcadia Ego》),以古希臘阿卡迪亞·尊石墓碑為主體。畫中,三個牧羊人圍著閱讀石棺上寫的碑文“Et in Arcadia Ego”(死神說:“我也在阿卡迪亞”),面色懷疑甚至驚恐,一旁的女子卻神色從容。普桑的這幅“Et In Arcadia Ego”引發了人們的各種猜想。英國研究學者亨利·林肯(Henry Lincoln)、邁克爾·貝金特(Michael Baigent)、理查德·雷(Richard Leigh)稱畫中暗藏圣杯的下落,且稱耶穌和抹大拉的瑪麗亞(Mary Magdalene)曾在法國南部一起生活,并誕下了法國梅羅文加王朝的國王。事實證明, “圣杯藏在墓中”的說法不僅是錯誤的,更一度使貝金特和理查德指控懸疑大師丹·布朗(《達·芬奇密碼》作者)剽竊其作品《圣血與圣杯》內容,卻最終敗訴。
揚·凡·艾克(Jan van Eyck),《阿諾芬尼夫婦像》(英國倫敦國家美術館)
據稱,美國畫家杰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曾在他最著名的一幅抽象畫中留下了自己的簽名,而在更早的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油畫奠基人揚·凡·艾克(Jan van Eyck)就經常用類似的方式為其作品標注。《阿諾芬尼夫婦像》中,阿諾芬尼夫婦身后的墻上就留有其精心寫成的拉丁文簽名“1434年楊·凡·艾克曾在此 地(Jan van Eyck was here 1434)”。而在背景中央的墻壁上,有一面富于裝飾性的凸鏡,放大后你會發現:從這面小圓鏡里,不僅看得見這對新婚者的背影,還能看見站在他們對面的另一個人,即畫家本人(畫家正在舉著右手向夫婦致禮)。
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最后的晚餐》(米蘭圣瑪麗亞修道院)
《達 芬奇密碼》可以說是丹·布朗(Dan Brown)對達芬奇的另類解讀。其中,丹·布朗大膽推測《最后的晚餐》壁畫中耶穌的情人抹大拉的瑪麗亞(Mary Magdelene)偽裝在他的門徒中。很多學者都否認了這一推測,稱施洗者圣約翰(St John the Evangelist)并非抹大拉,而布朗也堅稱圖中并沒有第十四只手。但這些都沒有阻止其他藝術歷史學家夸張的猜想。梵蒂岡研究學者嘉莉茲雅稱其已多方 位解讀出耶穌頭頂本月形窗戶隱藏的含義,稱其預示著4006年3月20日即將發生一場毀滅世界的洪災,一直持續到同年十一月一日,并標志著人類社會的新開始。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de Goya),《裸體的馬哈》(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館)
曾 西班牙調查局以淫穢為由沒收的《裸體的馬哈》,一直以來都是公認的最性感的作品。然而,畫中模特的原型也一直飽受爭議。一些藝術家認為西班牙半島戰爭時期 的首相,曼努埃爾·戈多伊(Manuel de Godoy)的情人是這幅畫的委托人。有人認為原型是阿爾巴公爵夫人,畫家曾為其傾倒,因此創作了這幅畫以慰相思;也有人認為畫中的女人是當時曾與畫家有 過婚外情的一位西班牙富商的妻子,不過最近一些學者因為公爵夫人的特點在畫家的畢生作品中多次出現否定了這一觀點。
提香,(Titian)《教皇保羅三世和他的孫子》(卡波迪蒙蒂天文臺)
提 香于1545年曾畫過保羅三世法爾內塞肖像,描繪陷入沉思狀態的老教皇。而這一幅是描繪教皇和他的孫子奧塔維奧(Ottavio)和亞歷山德羅 (Alessandro)在一起的群像:教皇正以懷疑的目光,沉靜的姿態,警覺地聽取奧塔維奧的訴說。年輕的奧塔維奧一副偽善和諂媚神態,掩飾著內心的殘 忍與冷酷,卑弓屈膝是為了獲得老教皇的信任;而后面立著的亞歷山德羅,則有著一副極為平庸無能的神情狀貌。現代評論家將其視作對教廷腐敗的批判。遺憾的 是,提香貌似一心想著如何幫助不爭氣的牧師兒子波尼奧(Pomponio),作品受到挫敗后便回到了家鄉威尼斯,留下了這部未完成的矛盾的杰作。
桑德羅·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春》(佛羅倫薩烏菲茲美術館)
波 提切利的這篇杰作禮贊了女神們的美及他們給人間帶來生命的歡樂,畫右邊(自左至右分別是花神、春神與風神)的三個形象以及畫中還500種可識別的植物物種 更是象征著春回大地、萬木爭榮的自然季節即將來臨。然而,藝術家對美好事物的愿望,總是與他所處的生活境遇發生矛盾。波提切利在畫上展示了那么多充滿著春 的歡欣的天神形象,也總不免帶著畫家內心深處所埋藏的一種無名的憂傷。這也被后人多方面地解讀為一個美第奇宮廷里的新柏拉圖主義知識分子企圖協調基督教、 猶太教、伊斯蘭教的野心,更有乖張的解讀將其視作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與六十年代加州的對立。后來,由于社會政治形勢的多變,加上波提切利的身份與眾不 同,在急劇的城市貧民與工人革命的斗爭聲中,美第奇被逐,宗教改革家薩伏納羅拉(Savonarola)被焚,這一切,使他感到恐懼與彷徨。而畫家的內心 憂郁,似乎都交織在他以后的繪畫創作之中了。
小漢斯·荷爾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兩個使節》(倫敦國家美術館)
衣 著整齊、穿粉色衣服的那個紳士看起來年輕、健康而自信,但從左下或者右下方看,便能看到一個對角扭曲模糊的骷髏。(其實這個扭曲的骷髏就是如今廣角攝影技 術中的物體成像變形而已。在繪畫中,這種技巧有個專有的名字叫做“視覺陷阱”。)盡管當時以死亡為提示的主題很常見,但為什么要用在這兩個來倫敦的法國使 節身上這個至今是謎。有人稱或許這幅圖原本是為了掛在樓梯井里的,以示路過的房主虛榮世俗的東西要不得。
約翰內斯·維米爾(Johannes Vermeer),《音樂課》(倫敦皇家收藏)
在 一個時期里,約翰內斯·維米爾(Johannes Vermeer)喜歡變化各種室內畫的表現方式,他總是畫有陽光的寬敞房間,陽光充足,整潔舒暢。《音樂課》就是這樣的作品。少女在教師指導下彈鋼琴,窗 明幾凈,舒適樸實。這幅畫色彩濃郁,響亮熱烈,復雜的紅、黑、黃、灰等,都統一在溫暖、平靜的基調之中。然而,從少女上方的鏡子中可以看出,她正目不轉睛 地看著畫中的男士。桌上的葡萄酒投手預示著感情的催化劑,而地板上的大提琴至今都被有性的象征,而我們旁觀者的這些觀點也將我們自己置于偷窺之境。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繪西斯廷教堂天頂畫》(又名《創世紀》)
《創 世紀》是米開朗基羅畫在梵蒂岡西斯廷教堂禮拜堂天花板上的巨幅壁畫,作品場面宏大,分成中央和左右兩側三個部分。近來有種說法稱畫中來自創世紀的九個場景 來自《圣經·創世記》,有著教會的意味,而圖中人物的姿勢又能夠拼出希伯來字母。大衛(David)和哥利亞(Goliath)來自“gimel”(在猶 太語里意味著力量)。對于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來說,他是想要極力溝通天主教和猶太教。其他的一些評論者大多是醫生,他們成功將天花板 廣闊空間里人的神經系統和必要的身體的部位平湊在了一起。
喬爾喬涅(Giorgione),《暴風雨》
自 然呈現著暴風雨欲來的陣勢,烏云滾滾,電閃雷鳴,但畫面上的人物,無論是哺乳的裸女,還是站立著的男人,都非常沉靜與安逸,營造出一片神秘、詭譎的氣氛。 這幅《暴風雨》引發了無數學者的猜想。畫中的男人被解讀成了士兵、牧羊人、吉卜賽人或是年輕的貴族,畫中的女人也被解讀成了貴族、妓女、夏娃、飛行中的瑪 麗。除此以外還有無數更夸張的猜想。那些專欄又是如何解讀的呢?用作家簡·莫理思的話來說,其主題深不可測,就像被作者附了身,神秘詭譎。